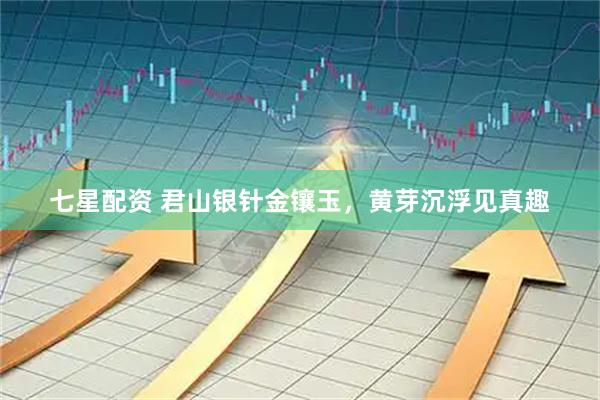
推门入室,先就觉着一股子温润的水汽,裹挟着极清、极幽的香气,扑面而来。这香不是花朵那种霸道袭人的香,倒像是从江南春雨后的竹林里,或是深山水潭边带着青苔的岩石上,一缕缕渗出来的,吸进肺腑里,五脏六腑都妥帖了。看杯中,水色是浅浅的杏黄,澄澈透亮得紧,仿佛盛的不是茶汤,而是一盅融化了、又凝固了的阳光。就在这片柔和的、金晃晃的底色里,一枚枚茶芽,笔直地悬着,不上不下,如同受了某种庄严的敕令,静静地定格在水中央。
这定格的姿态,便有了些“金镶玉”的气象了。说它是“金”,是日光与火工赋予它的魂魄,那浅金色的茸毫,在透亮的水里微微闪着光,确乎像缕缕金丝。说它是“玉”,是它那牙白至淡黄的芽身,温润、素洁、内敛,透着一种不言自明的贵重。金与玉,本是人间至华至坚的物事,此刻却这般轻盈地、梦幻般地,融合在一杯清水里了。富贵到了极处,反倒生出一种清寂的雅致来,不炫耀,不张扬,只在那里,便自成一个小小的、完满的宇宙。
我忽而记起前人两句诗来,说是“白银盘里一青螺”。那是以大观小,将偌大的君山,比作银盘上一枚青螺。眼前的景象,却恰恰相反。那杯中的一枚茶芽,微缩着,承载着的,不正是整个八百里洞庭与君山的魂魄么?你看它,这般安静地悬着,内里却是一场风暴初歇,一场生死的试炼刚刚完成。
展开剩余68%于是,我凝视的目光,便仿佛有了分量。那静止的茶芽,受不住这目光似的,微微一动——开始了。不是群起而踊跃,而是各守其时,自有章程。先是一两枚性子急些的,芽尖稍稍一颤,便似初醒的银鱼,摇头摆尾,悠悠地,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,向上浮升而去。它们升得很慢,茸毫舒展,仿佛一朵朵微型的金盏花,在无声地绽放。升到水面,便停住了,芽尖朝下,根根倒立,像一队悬停的、小小的钟乳石,又像古琴下垂着的流苏,静穆得很。
水底的呢,也不甘寂寞了。另一些茶芽,仿佛在杯底待得倦了,借着一缕看不见的水流,飘飘摇摇,也开始它们的旅程。只是方向是向下的,沉向那更深、更静处去。这一沉,便更显出一种庄重的、殉道般的美丽来了。它们的身影,在杏黄的汤色里渐渐模糊,化为杯底一层淡淡的、绒绒的金色,像是夕阳沉入湖心前,最后那一片辉煌的、温存的弥留。
更有趣的是那中间的。它们似乎打定了主意不参与这浮沉的抉择,只安然地悬在那里,像定海的神针,又像一颗颗垂直的、呼吸着的星辰。不上亦不下,不即亦不离,就在那“半梦半醒”之间,占住了一个最玄妙、最从容的位置。水波是极微的,空气几乎也是凝滞的,可它们就这样悬着,仿佛能悬到地老天荒去。
一杯水中,竟同时看见了“浮”、“沉”、“悬”三重境界。浮者,得其清扬,志在云霄,要将那最鲜嫩的气息,奉献给最先的唇吻;沉者,得其醇厚,甘居渊默,将一身风华,丝丝缕缕,都反哺给这一盏汤水,求一个底蕴深长;而那悬者,便是得了大自在,它超然于得失之上,风动也好,心动也罢,它自岿然,在动静之间,守住了自己的“常”。
这哪里是在饮茶?这分明是在观照一部无字的天书,一场微缩的人生。我们芸芸众生,在这尘世的波涛里,谁不曾奋力上浮,渴望崭露头角?谁又不曾失意下沉,体会过生命不能承受之重?然而,那最难得的,或许正是这杯中之芽“悬”的功夫。在命运的湍流里,在时代的沸水中,能不迷失方向,不随波逐流,于无数可能的轨迹中,找到并持守那条属于自己的、垂直的、安静的轴线。
我看得出了神。杯中的光影,不知何时悄然挪移了位置。那“金镶玉”的华彩,渐渐都化入了匀和的汤色里,浮沉也都歇了,只剩一片温润的、平和的澄黄。我这才端起杯,呷了一口。茶汤滑过喉头,初时是清,如山泉;继而是一点微微的、收敛的苦意,如人生必要的涩;旋即,一股绵长而幽远的甘甜,从舌底,从喉间,丝丝地泛涌上来,带着洞庭的烟水气,带着君山的竹露清响,久久不散。
先前的眼观之趣、心悟之趣,到此刻,才终于在身体里,落到了一个实在的、回甘的“趣”上。真趣何在?或许,就在这从绚烂华美的“相”,到纷然浮沉的“动”,最终归于平和澄澈的“味”的整个过程里。它不直接告诉你答案,只让你看,让你想,最后让你用自己的唇舌与心神,去尝出那个“真”字来。
一杯见底,齿颊留香。窗外的市声,不知何时又隐约地透进来了。方才那场静观宇宙般的出神,仿佛只是一个短暂的、金色的梦。但我知道,有些滋味与悟处,是已经沉在心底了。再繁华的镶金嵌玉,终要融入生活这杯平淡而真实的水里;再跌宕的浮沉故事,最后求的,也无非是心头那一缕悬而不坠的定力,与喉间那一丝历久弥甘的回味。
发布于:广东省珺牛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